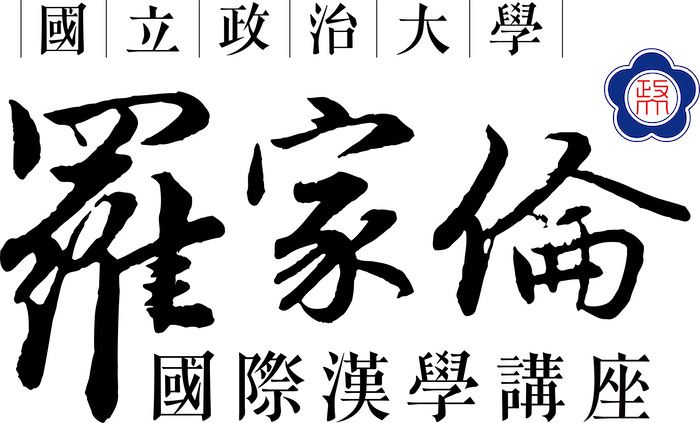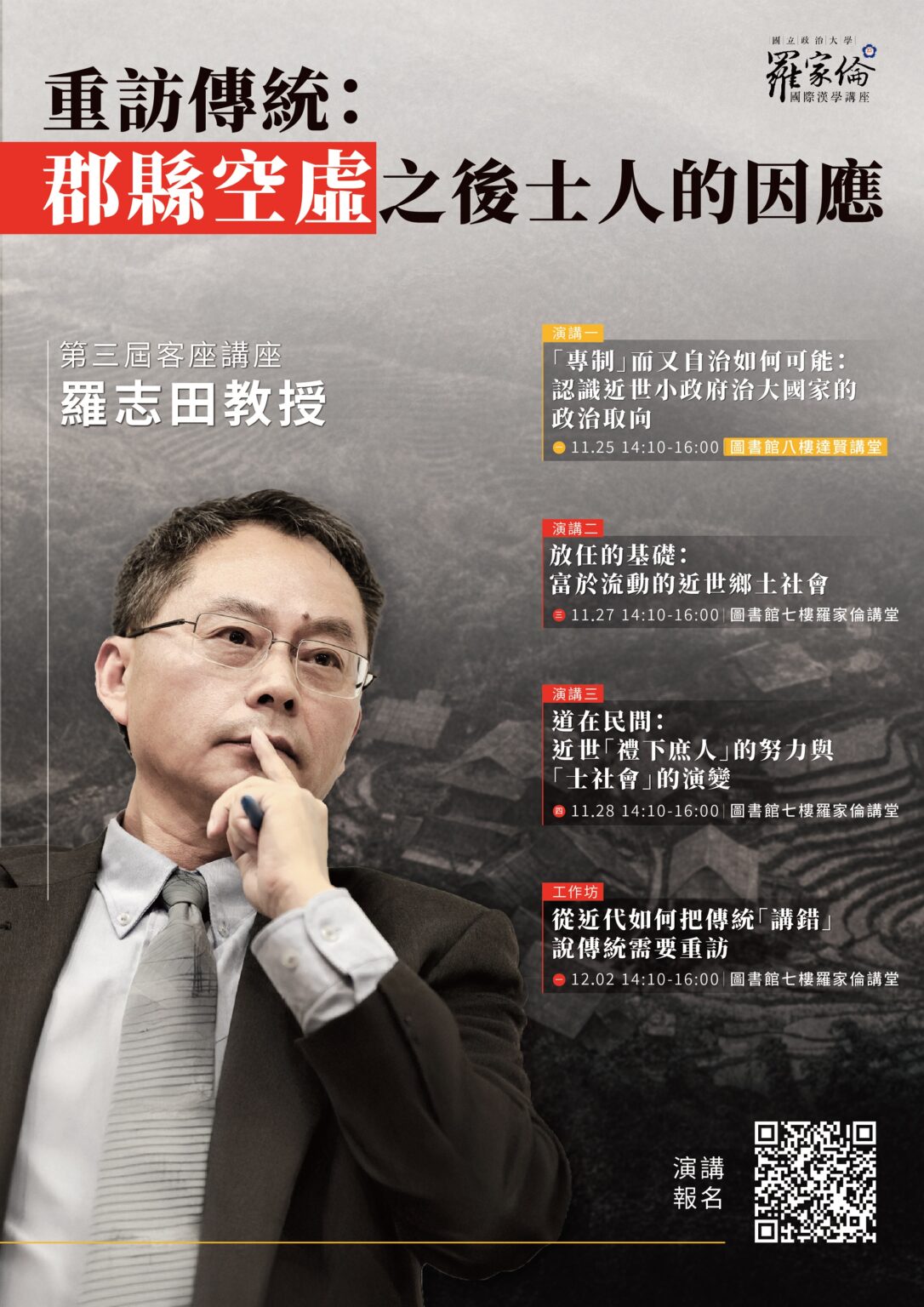【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】
本校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於12月2日,由中國四川大學傑出教授羅志田教授,展開「重訪傳統:郡縣空虛之後士人的因應」系列工作坊──「從近代如何把傳統「講錯」說傳統需要重訪」。
羅志田教授深入探討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,剖析傳統如何被重新詮釋甚至「講錯」,進而重新思考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認同。在西方文明衝擊下,中國接受「文明—野蠻」的觀念,並將國家困境歸因於自身文化,傳統因此被指為失敗的根源。特別是在1935年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中,傳統的內涵被重新塑造,表面強調自主性,實則反映主體性失落。
羅教授從內外部因素剖析傳統「講錯」的由來。內部來看,封建與郡縣治理模式的緊張導致經典理想與實際治理的脫節;外部則因西潮衝擊,中國從「天下觀」過渡為「國家—社會」框架,使官民關係與社會結構陷入緊張。西方學者如杜威從外部視角反觀中國歷史,卻也使傳統淪為被動的研究對象。
梁啟超在《新史學》中倡導「客觀」史學觀,五四運動進一步推崇理性與科學精神,甚至是被認為是東方文化代表的梁漱溟,也曾明確表示將傳統視為分析的客體。「傳統」成為了外部分析對象,而非內部認同的一部分。而章太炎則批評這種「客體化」態度,認為其將中國歷史「鄰家化」,忽視文化連續性,最終使本國歷史成為「他人的故事」。
在民族國家框架下,知識分子對傳統的理解出現矛盾。部分如常乃德主張移除情感與認同,保持理性;另一方,楊杏佛則強調應該在中國的立場批評中國,而非以外部立場完全否定中國。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提倡全球視角,強調世界公民意識;另一方面,這種視角模糊了「我」的定位,民族情緒與個人底線在「全盤西化」的表象下碰撞不休。
清末以來的改革與革命形成了對傳統的固定認知,這些認知推動了現代化,同時也導致傳統被「講錯」。重新審視傳統不僅關乎文化傳承,更有助於探討「我」與「我們」的身份與未來。
陳正國教授延續羅志田的研究,探討近代中國在傳統與現代化張力下的文化、身份與國際定位問題。他指出,十九世紀以武力與科技為「文野」標準,中國在應對國際秩序挑戰的同時,不得不重構傳統,但因語境差異而難以適應現代需求,陷入「講錯」困境。例如,「三代」概念作為理想參照,卻在制度與語言上難以契合當下。
近代中國的反思多以「他人本位」為出發點,如譚嗣同以西方為基準反思中國,卻較少以中國為本位審視他者。這涉及「體用之辨」的核心問題:何謂本體,何謂功能?制度作為文化的表現形式,如何平衡內外張力?中國改革中陸續出現以「新」為主題的各類文化運動蜂擁而起,它們皆源自傳統母體,但又試圖超越,成為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重要動力。那麼,胡適的《新潮》期刊以「文藝復興」為靈感,是否是一種中國傳統的重新詮釋呢?
羅士傑教授則從地方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角度,探討中國本體性與傳統的多樣性。他以溫州的日常生活和廈門小刀會事件為例,挖掘地方文獻中普通人的思想與書寫,展現「普通思想」的價值,拓展了中國本體性書寫的可能性。西方宗教、教育與資本主義對地方文化的影響,使地方經驗展現多元性,同時也挑戰了單一敘事框架。最後,羅教授引用三層次模型分析地方人士對自身、鄰里與上層文化的認知,揭示地方文化與國家互動的調適過程,強調重訪地方文化的重要性。
兩位與談人從地方與全球視角探討傳統,提供相輔相成的見解。羅志田教授指出,不同地區的中國傳統呈現形式可能迥異,例如四川的鄉村文化與福建形成鮮明對比。同時,他補充陳正國教授關於胡適的論點,指出胡適的文學革命著眼於民族語言建構,強調面向未來的「再生」,而非西方復興古典文化的歷史觀。這些視角共同豐富了我們對傳統的理解,並彰顯了地方經驗和全球視野在文化研究中的互補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