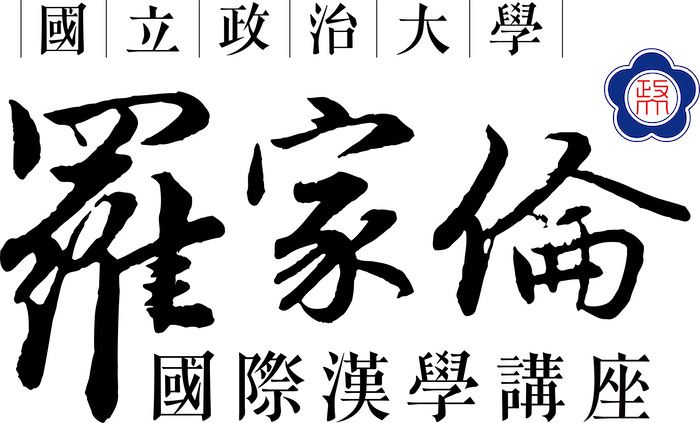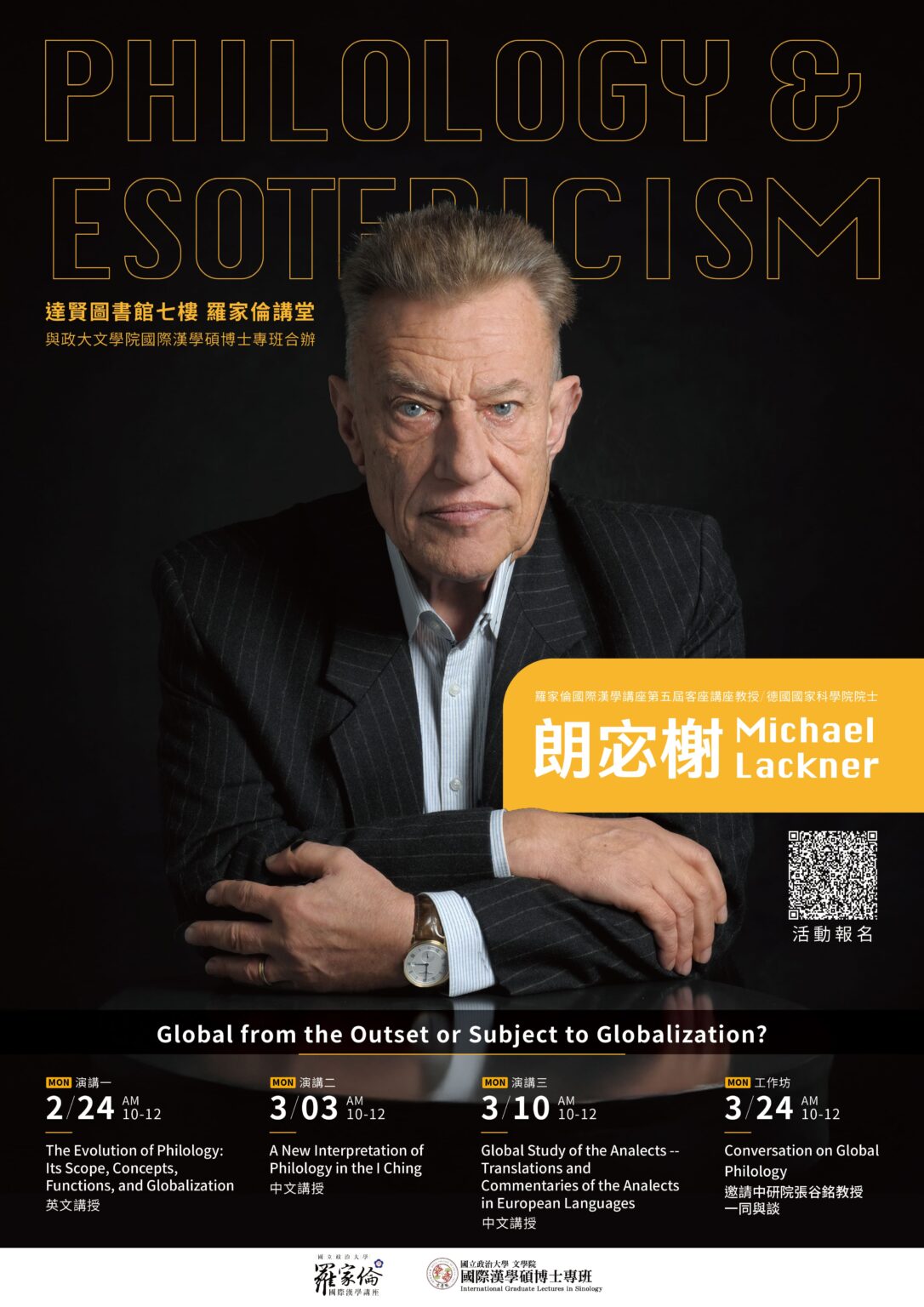【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】
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於3月10日邀請到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朗宓榭(Michael Lackner)教授,舉行「Philology and Esotericism: Global from the Outset or Subject to Globalization?」系列第三場演講──「Global Study of the Analects —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Analects in European Languages」「復調」的《論語》翻譯—以「仁」與「禮」為例。
首先,朗宓榭教授提出語文學對翻譯的重要性在於譯者不僅需要語言能力,還需要具備語文學的敏感性,尤其是針對文學和哲學文本的翻譯,需要超越字面意義,精準把握語意。
接著朗宓榭教授介紹《論語》在西方的翻譯歷程。從耶穌會對中國經典的翻譯開始,最初利瑪竇並未完成翻譯,而是期望儒家思想能與歐洲啟蒙互相結合,法蘭德斯耶穌會傳教士衛方濟向歐洲傳播儒學,翻譯時自己加段落,力求傳達儒學的內涵,與基督教區別,影響沃爾夫主張儒學與基督教教義應該互相對應,認同中國的道德體系是基於理性。然而沃爾夫強調因果關係和預定的和諧,被虔信派指責具有宿命論的傾向,因而受到普魯士國王腓特烈.威廉一世的迫害。
在《論語》的系統翻譯方面,理雅各、韋利等19世紀的譯者開始追求學術性的原文翻譯,林語堂等中國本土譯者也參與其中。二戰後,隨著現代漢學成為學術科目,《論語》的翻譯呈現多元化,近期的譯者更結合文本批判和考古學的研究成果。
由於《論語》的簡約語言風格有大量解讀空間,朗宓榭教授針對《論語》八佾篇中關於「仁」與「禮」的翻譯為案例進行分析。不同歐洲語言在各時期對於如何理解「仁」與「禮」相當多元,有的直接保留概念,不加翻譯,此舉增加了讀者理解難度;或是不翻譯「仁」,只翻譯「禮」。
另一方面,即使將「仁」進行翻譯,翻譯的結果也相當複雜。有的將「仁」與「人」進行字面上的翻譯;有的將「仁」的翻譯與權威連結;還有德文翻譯將「仁」翻譯成人性所需的美德,而法文翻譯將「禮」翻譯成神聖的習俗。在傳教士花之安為懂中文的西方學者撰寫一本手冊中,將「仁」定義為人與人之間的美德,呈現「仁」在社會的作用。中國譯者方面,辜鴻銘將「仁」翻譯成品德,「禮」翻譯成藝術;林語堂翻譯「仁」為真君子。有些翻譯如法西斯主義詩人龐德將「仁」翻譯成男子氣概,只能反應其意識形態,與原意相差甚遠;而有些翻譯如梅謙立的英文翻譯受到殷鐸澤的拉丁文翻譯的影響,參考了儒家經典,卻加上大量註釋,使得譯文貼近原意,但又過於冗長。
從《論語》陽貨篇中關於六言的分析來看,重點是「好什麼」和「學什麼」的問題,這在鄭玄、孔穎達和朱熹的注釋中對六言都有具體的解釋,但西方譯者都將六言翻成抽象的學問,只有耶穌會傳教士衛方濟則參考註釋做更具體的翻譯,殷鐸澤和梅謙立都參考中文譯本,這樣的現象揭示耶穌會傳教士基本上了解儒學經典。
《論語》中的核心概念「仁」、「禮」、「學」涵義深遠,翻譯的過程如同繞行孤島般對文本進行探索,這種外部性的視角會激發對核心概念的豐富理解,因此講者提出「復調」的《論語》翻譯,海外《論語》翻譯可以對中國經典作出新的詮釋。
在提問與討論階段,第一個提問者問朗宓榭教授如何看待「仁」是否包含女人的問題?講者回應拉丁語和德語的men也包含女性。第二個提問是關於如何平衡《論語》的歷史背景與譯者的歷史背景對文本的影響?講者回應儘管譯者都無法擺脫時代背景的侷限,但我們應該更深刻的考察譯者的歷史背景。第三個問題是關於譯者的宗教背景如何反映在《論語》的詮釋?講者回應在基督宗教不同教派會對《論語》做出差異化的詮釋,也會保留不同教派的詮釋。第四個問題是關於「禮」的翻譯是否比較固定?講者回應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,禮比仁的概念固定。第五個問題是關於對《論語》陽貨篇的翻譯似乎有斷層的現象?講者回應耶穌會的翻譯重視註釋,而現代翻譯忽略註釋,但具體的轉變時間還要再研究。第六個問題是關於希望講者介紹《論語》翻譯資料庫,朗宓榭教授則實際操作lunyu.de資料庫,介紹資料庫蒐集136本《論語》文本,包含50多種語言,可以進行系統性的比較研究。